《大西北从军记》| 北上16:退役
- 八大员题库
- 2022-03-23
- 149
- 更新:2022-03-23 10:40:12
北上16:退役
作者:段吉昌
不知道现在的新疆硫磺沟庙儿沟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乌鲁木齐昌吉八钢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心目中的军营还是朝气蓬勃热气腾腾,充满战斗豪情和青春气息;我们脑海里的西北城市还是原始朴实、具备坚定憨厚勤劳的民族气节;我们印象里的各族人民还是那样热情奔放,满怀纯朴的民族情怀名气大的八大员办理电话 。我们也热切希望能去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军营旧址转一转,看一看那些我们曾经寄予最大情怀、喷发最靓丽青春的那个平凡之地现在的样子,我们也希望那里能有一块纪念我们这个无畏的部队、怀念我们全体军人豪情的石碑,把我们曾经守卫那里的广大官兵的革命情怀,永远铭刻在西北广阔天地的那一偶。
退出现役是在我毫无准备、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连队里谁告诉我的我也忘了,绝对不是连、排、班长对我说的,也没有干部或那个人提前找我谈话或征求意见,一个连退伍战士那么多,不可能一个一个谈话或征求意见名气大的八大员办理电话 。总体流程应该和大的环境一样,由排长征求班长意见并统一口径后报连里,连里研究后逐级上报,最终由团里备案盖章批复。我的记忆是那几天营里赫副营长找我谈话,像是平时干部找战士谈心,拉拉家常,问问最近的思想情况,也没有直接说退伍的事,还重点询问了我写作上的事,最近发表了什么文章。他走后我还特意找了一些材料给连队写了一篇报道,抄写工整,找机会送到了昌吉报社。没想到那一次竟成了我在新疆的最后一次去报社送稿子,好在与当时的报社编辑李源枝和范晶见了面。李编辑高个子,人很和亲厚道,范晶热情大方还和我说话。他们两个那天就围在一张办公桌子上看划版纸,我放下稿子,站着说了几句话就出来了,匆匆赶回了连队。
退伍那会儿我还在二排五班,排长叫李志湖,山东人,个子不高名气大的八大员办理电话 。班长叫什么强,大个子,满脸胡茬,年龄看上去比连队里的任何人都要大一些,在集训队当教员,说话比较稳重老练,此前没在连队见过,好像从其它什么地方调过来的。五班实际一直由副班长张科祥负责,他是陕西凤翔人,我们同年入伍。确定退伍兵员一般由排长提议后报连里确定,再逐级上报批准,这是我在看到一些部队干部回忆文章中知道的。回忆退役这一个时期我感觉自己的记忆比较乱,只记得我和同乡的战友石宗宝去了师医院,我陪石宗宝看病取药,从师医院出来后我们一同去了师政治部宣传科见了叶干事,与叶干事走出师政治部时又遇见谢主任和一位干部,叶干事对谢主任说了我要退役了,谢主任说怎么会这样,给十四团政治处打电话留人吧,另一位干部说十四团一营今早已经宣布退伍名单了,谢主任长叹一声,去年不知道走了个刘干事,今年怎么又犯了这个错。随后我们俩又去了叶干事家,他的妹妹正在外屋用一个大盆洗衣服,叶干事整理了一些书籍和稿纸给我,鼓励我到地方后好好学习和写作。

从师部回连队,石宗宝埋怨了我一路,说我有这么好的关系怎么不利用,还说二排有一个兵,去年连队确定了要退役,人家有一个什么关系给连队打了个电话就留下了,今年退伍名单里还是没有名气大的八大员办理电话 。“你就是个死货”,石宗宝这样说我。最后连队的那几天,我能感觉了大家的诧异。一个表现良好,军事素质也可以,而且写作上有成就,大家比较看好的兵突然被退役了,大家的好强和不理解可想而知。我影响最深的是一位新疆籍老兵,四排时在一个排里,平时非常活跃,属能说会道的那种,在表演上很有天赋,这样的特长与我无形之中在心理上成为了知音,也是我心里的朋友。不知为什么他一直还是一个普通的士兵,连个班副都不是,我内心经常为他打抱不平。宣布我退伍以后,他的表现比较露骨,好几次我发现他和一伙兵在一块,一边用眼睛很神秘地偷看我一边和其它兵笑说,很诡秘的样子。我一直想不起在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位仁兄,这是我被宣布退伍时在连队记忆最深的事情。那时候我都算成熟的大人了吧,却没有记得去连部问问情况,或找连排干部说道说道,也没有记得找谁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就那么懵懵懂懂的等着退伍回家。
从离开家乡当兵第一天起,我们是怀揣着闯社会,将来找一个好工作成家立业而来的,经过部队学习教育,有了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名气大的八大员办理电话 。“这一百斤就交出去了”,这是服役的老乡私下里常说的话。还有一句话就是每每说起打仗,大家有一个共同语言就是:脑袋挂在裤腰带上了,随便拼。没有人说过害怕、逃逸之类的话,这与部队的宣传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关系密切有关。部队的几年,我们由懵懂青年修炼成有责任有担当有责任心的成年男人,也认识了世界的多面性。我们和连队确实有了感情,突然要离开心里还是感觉舍不得,比较空旷,又感觉无力回天。只能用平时受教育的口号暗暗地安慰自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就是我的家;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是平时喊得最响、次数也最多的口号。
离开部队时也是在早晨,有平时连队生活一样,迎着起床号声起床洗嗽、吃饭,打背包整理日用品名气大的八大员办理电话 。又迎着号声背起背包、提着大提包,排队到指定地点统一集合。最牵挂送别的还是留在部队的老乡,一大早就跑来告别,因为上课时间到了还是要听号声上课训练。想起来也挺寂寞,就跟着口令集合站队跑步再上车。统一集合点团部大操场红旗招展,有战士排队敲锣打鼓欢呼口号,还有首长和老兵帮忙将背包和大提包递上车,也有首长招手告别叮咛一路上注意安全,没有现在网络上发的那种互相抱头痛哭或流浪话别的场面,这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人情世故和野战部队坚韧不拔的作风。宣布退伍前我们听到了一些其它部队士兵退伍时的不好传闻,什么老兵与干部争吵干仗什么的;老兵在火车开动时握着自己排长的手不放等等。我们团直至整个五师那一年退伍工作平安顺利,在乌鲁木齐上火车,师团营主要首长都在场,分别站在几个车厢门口与退伍老兵一一握手个别。师政治部谢主任和叶干事及几位首长专门找到我们那个车厢和我及退伍兵握手告别,我自己也就那么傻傻地伸出手握一下,傻笑着道别。
离开新疆乌鲁木齐时,退伍兵乘坐的是绿色大客车,也是专门修饰一新的大车厢,一人一座,有专门的首长和老兵带队护送名气大的八大员办理电话 。几个省份的老兵同坐一列火车,只是分省市县扎堆而坐。我们可以通过车窗浏览所经过的新疆田园、大漠戈壁和城镇农舍,领略大西北更广阔的世界。其实回来时一路上的影响非常模糊,特别是吃饭睡觉什么的,没有了一点印象,也不知道是怎么解决的,可能是因为没有了去的时候那种新鲜感。在宝鸡市下火车,都没来得及和其它省市的退伍兵打招呼就被吆喝着下车排队点名出站,又被赶着上了早已等候地盖着大棚布的大卡车,连和凤翔战友握别的机会都没有。我记得离开新疆时买了几包新疆烟,好像再没买什么,回到家一共就带了不到四百元,其中退伍费是一百多元。所有钱按照当时的价值能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和一台标准缝纫机。如果用这个钱占媳妇(就是订婚),能付女方彩礼的三分之二。这就是当兵几年的全部经济收入,想交给父亲,父亲摇了摇头,让母亲保管,母亲说你自己拿着准备结婚用吧。
回到县城的那天是个上午,这也是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事情名气大的八大员办理电话 。县城的西门口出现了一个大转盘,这是入伍前没有的,街道还是土房土街道,街道边上还长了小草,有些空地上杂草丛生,街面上垃圾满地。从县武装部集体签到出来,很惊喜地碰到生产队的两个社员,一个是生产队保管员李金锁,五十多岁,中等个儿,很本分很老实,自我记事起他就在生产队任这个职务,有时还兼任打麦场场长,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另一个是比我大两三岁的社员李福会,个子不高,话也少,非常老实。他们俩给生产队买完农具准备回家,看见我很高兴地叫了一声,我赶紧接上话打招呼,说自己退伍了,准备回家,两人轮换着帮我拿上提包,我自己背上背包,出了县城南门向东南原步行前进,一路上背背包的退伍军人也有好几个,路人都好奇的向我们张望,我们也是小县城里的一道风景啊。
回村后的第二天还要到县民政局登记报到,就是在县政府大院里第二栋平房里的一个办公室的一个登记册子上写下自己的部队番号和家庭住址名气大的八大员办理电话 。来登记的退伍兵很多,都是结伙去的,轮到我登记时,负责登记的闻同志反复问我在部队有什么特长,我说是步枪手,他又大声问:还有什么特长?我又重复一遍,他瞪我一眼让我一边去。这时候我才注意到退伍证上填的是“步枪手”,后悔自己没能在退伍时到连队文书那里好好看看,后来听在电力局工作的族叔说民政局老闻说部队交兵的领导还特意交代了说我有写作特长,可惜我思想不开窍,没有趁热打铁去找老闻联系,白错过了一次机会。当时还有退伍兵登记了部队的患病证明,是我们一个连的战友,让我感到很突然也很吃惊,在部队时没有听说他患什么慢性病,据说部队退伍时发了病历证明和补助,到地方凭证明继续领补助。那天从县民政局出来还碰见了送我去当兵的大队支部书记,他在县政府第一座平房屋顶上,和他们生产队的副业队一起干活,这让我吃惊不小,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竟然和社员一样一身泥巴干体力活,这个画面一直留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也是我后来极力回避当农村生产大队主要干部的原因,因为在这个支部书记之前是我亲伯父任大队支书,伯父之前是我一个族爷爷,在职时也是和其它社员一样一身泥巴一身汗参加劳动,离职后靠自己体力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干不动了也没有什么收入,就只能靠儿女养老送终。尽管政治宣传上说什么不管什么岗位都是为人民服务,我的心里还是想有个挣工资的体面工作,不想一辈子呆在农村里背太阳,这是当时的我以及每个农村青年心里所想的,尽管当时的报纸广播天天讲扎根农村干革命。生产队以农业生产为主,各生产队天天抓上劳人数,没有特殊情况绝不请假,连续旷工的要在晚上生产队的社员大会检讨,严重的还要召开批斗大会。我在完成了退伍兵登记手续后,到舅家姑家姨家姐家走了几天亲戚,了解了父母心愿和农村传统习惯的习俗,就开始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为的是挣生产队每天十分的劳动工分,也帮助父母处理一些琐事,以减轻父母的家庭负担。
记不清是退伍回家后的某一天,村上有人捎话喊我赶快去大队办公室,是公社来了一个管宣传的干部,让我第二天去公社找书记,说是县委宣传部打来电话,某某村有个能写作的退伍兵刚回到家乡,让公社重视一下名气大的八大员办理电话 。他们之间具体怎么说没人详细告诉我,但部队政治部的一个普通公函,就这样从县委宣传部通知到公社书记,再由公社通知到大队直至我的家庭和本人,可见那个时候的政府机关办事多么是认真负责。第二天我去公社,公社书记说师政治部给县委宣传部发了函介绍了我的写作情况,让我先别乱跑,回村后好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好好表现。他还喊来公社放大站播音员与我见面,一位上身也穿着绿色女军装,说话声音洪亮且有节奏的西安下乡女知青。又过了几天我被喊去见书记,书记说上面有文件让精简县社办人员中的八大员,当社办人员是不行了,让我在队上继续好好参加劳动,或者先进大队班子当个一般干部,有机会在安排能发挥写作特长的工作,别像有些退伍兵,回来后不好好参加生产队劳动到处跑,搞得自己名气不太好。这个书记叫张建忠,一位了不起的实干家,他最大的政绩是让我们家乡那个大小台田横七竖八的东南原变成了块块田地四方四正的方块田,被县市省作为“园田化”的样板推广。张书记后来当了县委副书记,又到其他县当县委书记,直至省委政法委某部门领导。张书记当时说的都是实在话,那个时候讲政治,注重实干看日常表现。没过几天我就被安排到县委农业学大寨办公室,接替一个因犯错被开除的工作组副组长的工作,参加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并任工作组副组长。“上任”的那一天,我早起在农村家里吃了饭,继续穿上绿军装,斜肩挎着军用绿挎包,背起打好的绿背包,步行三十多里,农村吃中午饭前,来到了我退伍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天成镇韦家庄大队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第一个迎接我的是大队广播室播音员白国莉,一位高个的西安三五零七厂下乡女知青,她带我到工作组驻地,一户主人在外工作的农家小院,工作组组长苟宝善热情接待了我。苟组长当时任县水利局副局长,后来任局长。苟局长在那个晌午,带我以县上下派干部身份到农户家吃了有生以来第一顿农家派饭。工作组组员还有县审计局干部沈进贤、县药材公司干部杨海峰以及麦枣峪村闫东定,老沈老杨都是在国家正式单位任职的骨干,后来都当了单位主要领导,就我和闫东定是以农村积极分子身份参加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按照后来我看到的中央文件精神,参加农村基本路线工作队的农村积极分子,可以随时补充到户口所在大队的领导班子任主要职务,特别优秀的可吸收到国家机关工作。
那一年我的月基本工资是十八元,粮票三十斤,每天吃派饭,每天付给农户伙食费三角,粮票一斤,剩余九元钱交给自己户口所在生产队,再由生产队记工日三十个,也就是三百分工名气大的八大员办理电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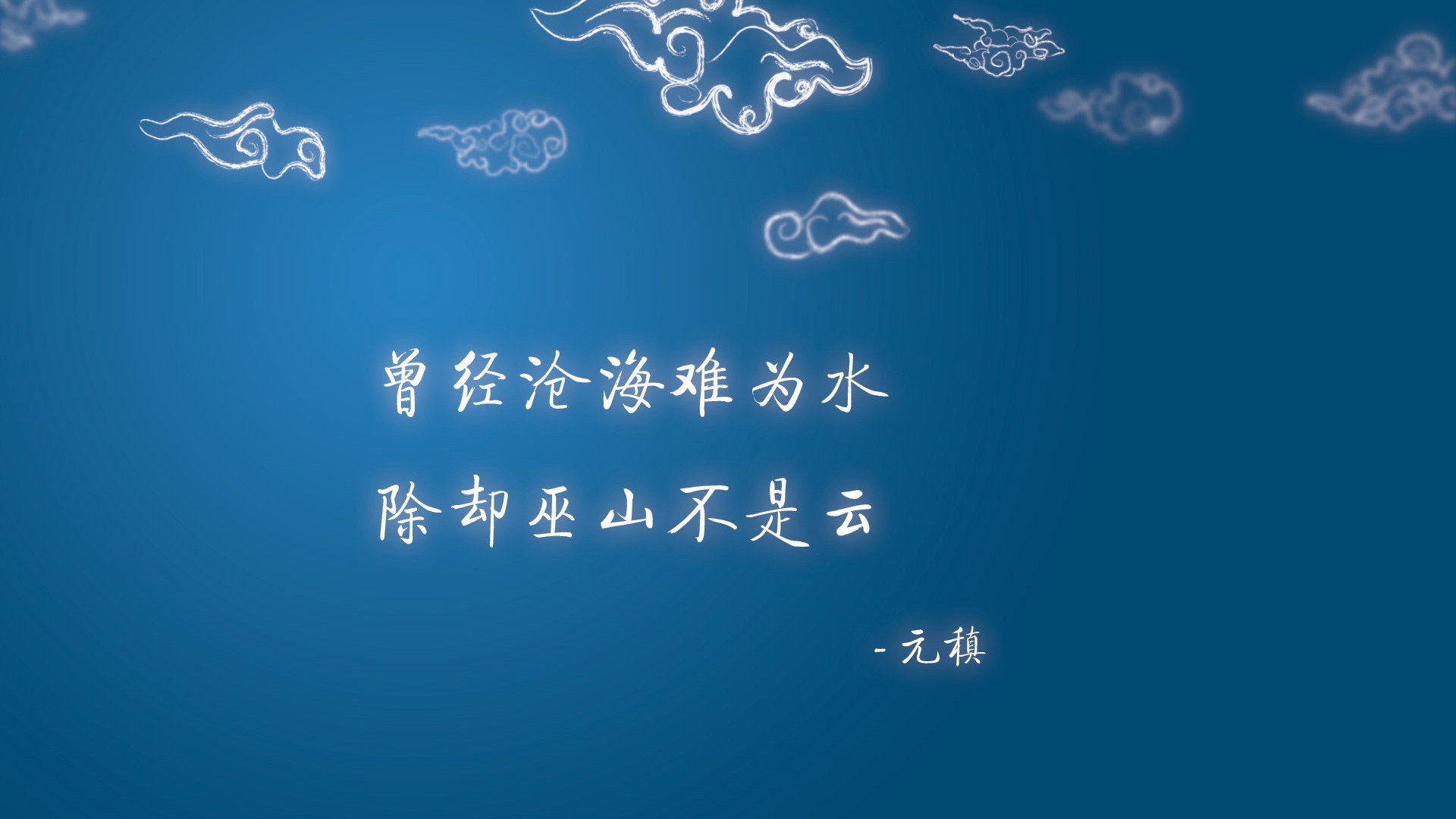
西北从军这一段就写到这里了,在部队的几年,没有干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但完成了人生中的又一次转变,是值得铭记的名气大的八大员办理电话 。要说服役几年有什么体会的话,那就是:部队这个大熔炉可以锻炼人成就人,特别是青年士兵,可以完成人生由:“嫩”到“强”的根本转变,也是一次人生飞跃。通俗点说,部队也与地方一样,技术好工作好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还是人要灵活,能见风使舵,就像一些当领导的所说,忠诚度远远大于工作能力,所谓忠诚度就是人的灵活性,大多数懵人在生活中的表现是内向,集体大众生活中遇事不知所措,导致动手能力差,一旦明白了某一件事或某一个动作或认准某一件事,容易形成一种机械性操作,主动反复的去做,而且会越做越好,而在人际关系中显得极为木纳。如果是有特长的懵人处在一堆普通人之中,则容易被人误解为骄傲看不起人或高傲自大。从这个角度出发,在官场、在一些政务和事务性场合,懵人是吃不开的。这是大实话,也是大家一直都知道,却不愿公开说的话。
记这样的流水账,无非是从个人角度、以个人观点、个人自身的认知,用文字留下一些个人的记忆名气大的八大员办理电话 。因为要公开,就从正能量的角度写了一些正面的东西,避开了那些不能给人启发教育的琐碎,也是希望能给自己反思借鉴的镜子,绝没有炫耀或自夸或自我显摆的意思,语言也非常平庸,情节非常直白,整个章节段落平铺直叙,没有什么惊心动魄或大起大落或跌沓起伏。留下自己的文字,记录一段人生历程,了却自己的一个心结,是为终。

